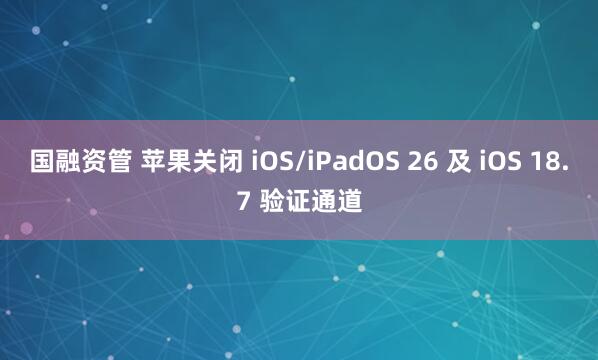智慧财讯 余世学:播种凉山三十八载

还有一年,59岁的余世学就要退休了。廉政瞭望·官察室记者见到的他虽坐在办公室里智慧财讯,却穿着一双适合下地干活的老布鞋;他戴着一副眼镜,有着文化人的气质,却手掌粗糙。
前不久,他才从木里藏族自治县屋脚乡回来。作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研究员,他刚完成凉山州农业科学院一个马铃薯项目的验收工作。测产数据显示,“川凉薯17”亩产高达3888公斤——这个数字,比他38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翻了番。
“那时候,玉米亩产400公斤就算高产了,马铃薯能突破2000公斤就很不得了了。”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激动。
1987年7月,21岁的余世学从四川农学院(今天四川农业大学)农学系毕业,按分配政策来到凉山州农技站。他是凉山盐源人,祖籍冕宁,从考上大学那刻起,就注定要回到这片土地。
“远看像要饭的,近看像挖炭的,走拢一问是农技推广站的。”他至今记得当年形容农技员的顺口溜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凉山,交通闭塞、物资匮乏,农业技术推广还在起步,条件艰苦,农技员工作起来就是被调侃的那种狼狈样。
文 |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李浩瑄

余世学(右一)在超级杂交稻单季每公顷19吨高产攻关德昌基地收水稻。
驻点:与土地相熟
刚到农技站,余世学被安排到海拔2380米的布拖县则洛乡(现划归至特里木镇,为则洛村)驻点。
“乡上没有班车,离县城将近4公里,要么走路、要么骑单位配的自行车到县城,再坐班车回西昌。”他每月只有发工资那几天回一趟家,领了现金又匆匆返回。驻点的日子,余世学和前辈们承担起全国荞麦、马铃薯、玉米等试验项目,还培养了十几名彝族农技员。做试验、干体力活时召集农技员一起;室内分析、考种这些技术活,则自己动手。
“他们大多小学没毕业,不识字,只会彝文。”余世学说,当时全靠一位叫吉斯古格的彝族“老革命”当翻译,“他是最早培养的农技干部,汉语很熟练”。
1988年春天,农业部“温饱工程”在则洛乡试点玉米地膜覆盖技术——余世学告诉记者,这项技术在1985年才引进凉山,起初只是小范围试验,他参加工作时正好赶上大面积推广的起步阶段。他跟着当时的副站长魏太忠、点长吴志金带着农技员挨家串户做动员,有老乡堵着门摆手:“地膜要钱,化肥也要钱,种砸了咋整?”余世学和其他驻点人员向局领导汇报后决定赊销农资:春天先把地膜、肥料赊给老乡,秋天收获玉米后,要么卖粮还款,要么直接用玉米抵扣。“当时彝族老乡收入低,连吃饭都成问题,只能用这种方式帮他们迈出第一步。”余世学说。
做试验的播种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,“不然没法对比数据,就算加班加点也得干完,不像农民可以第二天再弄,那时候没有自动化工具,全靠手工。”
有一次,余世学一锄头下去铲到了自己的脚趾头,指甲盖都翻了,带他的前辈找了树上的藤蔓给他敷上止血,“还真有用,没条件消毒处理,但也没感染,就这样慢慢恢复了。”
那年秋收智慧财讯,1000多亩地膜玉米黄澄澄铺在山坳里,亩产达450公斤,是传统种植的两倍,彝族老乡背着最好的玉米棒往乡政府送。也是这年,他和团队在乡上配给的科研“自留地”,把老站长从内蒙古带回的薯种“克疫”实生籽培育成“凉薯14”——这个抗晚疫病、煮着吃又粉又沙的品种,至今仍有农户在种植。
“现在市场上主推的是‘青薯9号’,产量还要高些,但老乡还是喜欢‘凉薯14’的口感,种来自己吃。”他说。
坚守:对土地长情
在凉山,农技推广不只是技术活,更是人与人的交道。余世学记得,每年11月收完玉米,老乡杀猪都会给驻点送肉,“我们去村里也是被热情招待,他们喊我们喝水,还给我们做饭。”
1989年去雷波下乡,余世学等人走到一户老乡家找水喝,对方直接锁上门不让走,杀了鸡留他们吃饭。“最后还是吃了才走。”也是这些瞬间,让余世学愈发坚定自己当初的选择。
余世学并非没有失手。
20世纪90年代在西昌市兴胜乡搞莲花白后茬玉米高产试验,余世学听老乡任吉林说地里没有地下害虫,就没坚持要求药剂拌种。结果玉米出苗后,全被“小地老虎”啃光了。
错过了播种季节,补种后也达不到高产目标。“那次是真的特别丢脸,跟领导汇报,领导让我吸取教训,我又去跟老乡道歉,老乡倒是很豁达,跟我说‘种庄稼不好也就是一季的事’。”从那以后,余世学明白技术方案不能打一丁点的折扣。“之前布拖地下害虫并不严重,没想到在兴胜乡这边是突出问题,这也让我知道技术还得因地制宜。”
后来他主持玉米高产攻关,想在亩产1吨以上突破,却多年未果。2008年在盐源搞“攀西地区增粮增收工程”时,他已当上农技站站长,却因品种和气候问题,亩产只有900多公斤,始终差了一点。
“最终是省农科院的老师突破了亩产一吨的目标。”他语气中没有不甘,只有欣慰,“出成果,是为了造福百姓,谁成功都是成功。”
凉山的土地到底适不适合种粮?
余世学引用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话:“顺天时,量地利,则用力少而成功多;任情反道,劳而无获。”他说,农业不是蛮干,是科学。
尽管挑战仍在,诸如凉山仍然存在机械化程度低、季节性缺水、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,但他对凉山的农业未来充满信心。他相信,随着家庭农场、智慧农业的推广,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土地上。
38年间,余世学不是没有机会离开。
“当时搞专业的人少,很多人从政、改行或留在城里。”但他留下了。他说,是老站长魏太忠和前辈吴志金那样的人影响了他。
吴志金比余世学年长几岁,彝语说得好,常年蹲点基层。1993年,他在乡上因意外成为植物人,三年后去世。
“我们后来评成果,都把吴志金排在前头,算是对他的纪念。”余世学说,“看到老乡从吃不饱到能吃好,那种成就感是实实在在的,我没有理由不坚守在这片土地上。”
挑战:新的角度看土地
在基层干了几年后,因办公室一名干部退休,字写得还行的余世学被调回州里。
“办公室工作很杂,不再局限于高山作物,水稻、小麦都要管。”他说,38年工作中,印象最深的仍是在基层那几年,“虽然艰苦,但出的成果很有意义。”
后来先后当上副站长、站长,余世学早已不是那个骑着自行车下乡的年轻人。作为站长,他的职责更多在于组织项目、主持验收、撰写建议,但他从未离开土地。2013年起,余世学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,履职十余年间,他的建议始终沾着泥土、带着稻香、冒着热气。
随着生态好转,野生动物频繁“下山抢粮”。“野猪、猴子成群结队,老乡半夜要起来敲盆驱赶。”余世学说。他在调研中发现,理赔程序复杂、补偿标准不统一,严重打击了农户种粮积极性。
2025年1月,他作为四川省人大代表,提交了《关于建立省级野生动物损坏农作物赔偿机制的建议》,呼吁加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、简化理赔流程、研发防御设施。
“我们不能只让农民承担生态保护的代价。”与此同时,粮价低迷、种粮收益不高,也让他忧心。“现在,稻谷才两块多一斤,玉米一块多,靠种粮供孩子读书都难。”他建议推动“粮经轮作、套种”模式,如在冕宁推广“粮烟复合”种植,既保粮食生产,又增农民收入。
“当上人大代表后,眼界变了,以前只关注农业技术,现在会看计划报告、预算报告。”这些年,在余世学看来,凉山农业没有突变的转折,只有渐进的改善。
取消农业税后,老乡种粮积极性提高,凉山从2004年起连续19年粮食增产。2020年,凉山全面脱贫。余世学的工作重心也从“温饱”转向“致富”。他参与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,推广高标准农田,参与超级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项目。
从关心能否吃饱,到关心大家能否吃好,再到现在怎样才能种粮致富……余世学亲历了作物产量的跃升:从玉米亩产400公斤、马铃薯突破2000公斤就了不得,到如今德昌的袁隆平团队水稻亩产1251.5公斤,盐源玉米亩产1248公斤。
农业机械的普及更是天翻地覆:“以前种洋芋靠牛犁,现在播种机、微耕机都普及了。”

至今,余世学仍行走在田间地头。
38年,足够一个生命从出生到中年,也足够一片土地从贫瘠走向丰饶。长达300多公里的安宁河,从崇山峻岭的小涧,汇聚成悠悠长河,滋润着大河两岸平坦的沃土田畴,造就了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谷平原。
如今,安宁河谷平原以其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被誉为“天府粮仓”凉山片区。余世学是千万农技人员中的一个。他们用一生,在凉山的褶皱里埋下种子智慧财讯,迎来一个又一个丰收季。
优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